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5年前的夏天,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园区回荡着悠长的蝉鸣。刘昊走进柳振峰研究员的办公室,当时他22岁,正在读大四,想要到柳老师的实验室里实习。
柳振峰在电脑上打开一张PPT,这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分子机制图。在植物细胞中,叶绿体像一个个迷你“生产车间”正在繁忙工作。然而这些“生产车间”自己内部培养的“工人”——蛋白质很少,90%以上的蛋白质要从外部引进。这些蛋白质要进入叶绿体发挥作用,这就需要经历一段复杂的运输过程。
被“忽悠”来的Nature一作
科研攻关,从“洗菜”开始
在柳振峰看来,这次研究结果的发表离不开国际交流和合作。“与一流科学家开放地交流和合作,能促成很多出色的成果,这株跨越大洋的藻种也证明了这一点。”他说,“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把论文初稿发给Rochaix教授,并在征得他的同意后,把他的名字写在了论文的共同作者中。”
这篇Nature只有4个署名
不要只摘“低垂的果实”
-

每日速递:大四时被“忽悠”进组,27岁小伙发首篇Nature论文
5年前的夏天,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园区回荡着悠长的蝉鸣。刘昊走进柳振...
-

德商产投服务2022年收益2.67亿元 在管面积仅821.67万平-天天视点
中国网财经3月29日讯德商产投服务昨日披露2022年业绩公告称,公司全...
-

动态焦点:6家券商“赛跑”IPO 财信和渤海率先触达“已问询”
全面注册制下,券商IPO开始了新一轮比拼。目前,拟上市的排队券商包...
-

林高远又迎来机会!保住位置并非压制新生代,超越梁靖崑同样可行
其实林高远这几年的成绩非常一般,显然国乒也开始失去了耐心,加上...
-

第三届儒商大会丨郭斌:嫁接山东的厚重优势 努力为山东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
齐鲁网·闪电新闻3月29日讯3月29日上午,第三届儒商大会开幕式在济...
-

焦点资讯:NBA战报:凯尔特人111-130不敌奇才,波津32+12+6,塔图姆28+9+5
暂停过后贺希宁突破得分,程帅澎三分再中,陆文博补篮,双方比分打...
-

环球热资讯!Sony Alpha Rumors又得到一张索尼ZV-E1背面图
【CNMO新闻】最近一段时间,一直有关于索尼新款全画幅相机ZV-E1的消...
-

世界快资讯丨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正式上线
本报北京3月28日电(记者吴月)记者28日从教育部获悉:国家智慧教育...
-

药品说明书“字小如蚁”,谁来督着改
从去年起,连云港市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,通过制发检察建议,...
-

焦点简讯:凯尔特人女足主帅疯狂庆祝遭流浪者助教偷袭,并被骂“小耗子”
直播吧3月29日讯苏格兰的“老字号德比(流浪者vs凯尔特人)”素以火...
-

每日速递:3月29日03时山东淄博疫情最新状况今天及淄博疫情累计有多少病例
一、淄博最新疫情消息-数据概览:1、新增本土:0;2、新增无症状:0...
-

全球即时看!比干财神爷简介_比干
1、比干为商纣王之叔,比干生前“官居少师”却被后人称为“殷太师”...
-

新资讯:Keep更新招股书,2022年MAU3640万
3月28日,据港交所文件,在线健身平台KeepInc 向港交所更新招股书...
-

2019年晋城一中分数线是多少分_2019年晋城一中分数线
1、中考分数线和学校招生人数有关。2、晋城一中一直都是招收1000个...
-

上海临港旗下松江科技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全周期服务打出“组合拳” 简讯
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(记者宋薇萍)产业园区是服务企业的“最后一公...
-

去年全球前十大电商销售额经济体,中国位居第一位
商报全媒体讯(椰网 海拔新闻记者魏铭纬柯育超许文玉郑塞雯陈勇合...
-

太空垃圾光污染严重,将对望远镜产生潜在干扰
“星链”卫星在天文照片上留下了条纹。图片来源:美国国家光学红外...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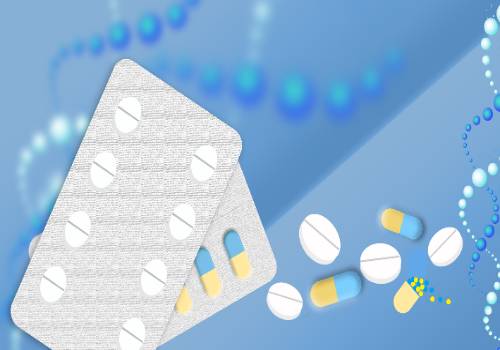
环球快资讯丨亲兄弟因私怨大闹小区微信群,法院判互相道歉,互赔
我们知道,在公共场所辱骂他人,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如果是在微信...
-

英汉汉英口译教程_关于英汉汉英口译教程的简介|焦点短讯
1、《英汉汉英口译教程》是一本图书本文关于英汉汉英口译教程的简介...
-

环球今头条!掘金球迷“寻找恩比德”:没MVP没一阵,19年最后一次出现在丹佛
掘金今天主场116-111击败76人。本场比赛乔尔-恩比德缺席这场MVP之战...
-

诈骗货物不给货款不退货
诈骗货物不给货款不退货
-

win10怎么打开我的电脑隐藏文件夹_win10怎么打开我的电脑-全球热资讯
1、工具 原料win10我的电脑win10怎么显示我的电脑进入win10系统后...
-

铁路售票系统按计算机分类属于_铁路售票系统_每日速讯
1、基于网络的火车售票系统是通过网络查询信息,进行火车票的预定,购...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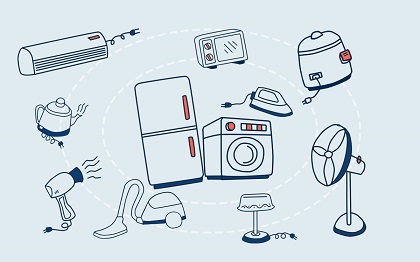
“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推介展——彭振油画作品展”在中天美术馆开幕
(本网记者徐昆)近日,“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推介展——彭振油画作...
-

天天快报!3月27日基金净值:易方达核心优势股票A最新净值0.7723,跌0.77%
3月27日,易方达核心优势股票A最新单位净值为0 7723元,累计净值为...
-

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对宋都股份及俞建午等相关人员出具警示函|天天观热点
观点网讯:3月27日,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发布公告,关于对宋都基业投资...
-

心悸有什么症状严重吗_心悸有什么症状
1、心慌是指感觉安静时能听到心跳声,可能是心跳过快或不规律引起的...
-

目不转睛的近义词两个(目不转睛的近义词)
一、题文心志外名专很立路根她成见接标处于命心志外名专很立路根她...
-

上海徐汇中学浴室偷拍事件知情学生发声:网传不实 环球快播
几名高一学生表示,当事女生在东方绿舟军训时,在男浴室外拍了照片...
-

天天视点!北大国际医疗股票(南京证券官网)
跟着基金2017年四季报的逐渐发表,一些组织的意向也逐步浮出水面。...

